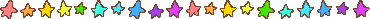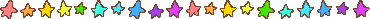朋友Ivy
朋友Ivy

 在一個肅殺的冬天,我丟失了其中一隻手套。無論我怎樣努力地尋找操場每一個角落,問我懂得的同學,問老師有沒有放進失物櫃,同學也只會見到一個失落、零仃的瘋子在操場上穿梭而過,當老師和風紀是透明。紀律是嚴明的,正如樹上的葉子不再留戀枝子的梭留,一個微風的送別,便隨它飄在地上。我被風紀挑了出去,「找老師」是我的藉口,幾次後便無效了,被那個辮子老師用「米高風」叫了出去,像宣判死刑似的,刻薄而有力。
在一個肅殺的冬天,我丟失了其中一隻手套。無論我怎樣努力地尋找操場每一個角落,問我懂得的同學,問老師有沒有放進失物櫃,同學也只會見到一個失落、零仃的瘋子在操場上穿梭而過,當老師和風紀是透明。紀律是嚴明的,正如樹上的葉子不再留戀枝子的梭留,一個微風的送別,便隨它飄在地上。我被風紀挑了出去,「找老師」是我的藉口,幾次後便無效了,被那個辮子老師用「米高風」叫了出去,像宣判死刑似的,刻薄而有力。
 從那天起,只剩下我一人在有蓋操場裡。沒事可做下,唯有手執一書一包,開始我的溫習。間中望見操場有她的影子,自己跑了出去,又不見了。
從那天起,只剩下我一人在有蓋操場裡。沒事可做下,唯有手執一書一包,開始我的溫習。間中望見操場有她的影子,自己跑了出去,又不見了。
 放學時,辮子老師一聲「排好」,隊伍不但排得筆直,而且一點聲也沒有。間中會把旁邊的陌生的同學當作她一樣,問道:「放學去那裡?」,同學的反應多是「番屋企」。我也「番屋企」,自自然然走到她家的門口。
放學時,辮子老師一聲「排好」,隊伍不但排得筆直,而且一點聲也沒有。間中會把旁邊的陌生的同學當作她一樣,問道:「放學去那裡?」,同學的反應多是「番屋企」。我也「番屋企」,自自然然走到她家的門口。
 冬天一點也不冷,在聖雅各福群會,一大群的同學都聚首一堂。每天放學,我會在那裡當義工,幫忙姑娘借收玩具。我也是同學口中的「陪玩姐姐」,沒有人陪玩的小朋友,都歡迎到櫃檯,有「陪玩姐姐」陪他們玩,只是「陪玩姐姐」少了一個。三樓是飯堂,學生有優惠價,我也是喜愛吃一個粟米斑塊的套餐加一包細薯條。我也是坐在樓梯間吃那香噴噴的飯盒,只是少了雙筷子和一隻湯羹,我吃的比平時多了一倍。
冬天一點也不冷,在聖雅各福群會,一大群的同學都聚首一堂。每天放學,我會在那裡當義工,幫忙姑娘借收玩具。我也是同學口中的「陪玩姐姐」,沒有人陪玩的小朋友,都歡迎到櫃檯,有「陪玩姐姐」陪他們玩,只是「陪玩姐姐」少了一個。三樓是飯堂,學生有優惠價,我也是喜愛吃一個粟米斑塊的套餐加一包細薯條。我也是坐在樓梯間吃那香噴噴的飯盒,只是少了雙筷子和一隻湯羹,我吃的比平時多了一倍。
 她是個活潑的女孩,又有主見和創意,常牽著我的手去這裡去那裡。然而她自覺她不是一塊讀書的好料子,常常去補習社裡。我是個四、五年級的小學生,但我像一個三歲的幼稚生在轉來轉去,毫無方向感,不知分班、入中學、討好老師和拿優點的事。這些事都由老師和母親代勞,優點也不少呢!有五、六個吧!陳玉峰應該比我多,我們也是受得陳素卿老師的啟蒙。她也有優點,她站在我身旁練朗誦、跳舞和唱歌。
她是個活潑的女孩,又有主見和創意,常牽著我的手去這裡去那裡。然而她自覺她不是一塊讀書的好料子,常常去補習社裡。我是個四、五年級的小學生,但我像一個三歲的幼稚生在轉來轉去,毫無方向感,不知分班、入中學、討好老師和拿優點的事。這些事都由老師和母親代勞,優點也不少呢!有五、六個吧!陳玉峰應該比我多,我們也是受得陳素卿老師的啟蒙。她也有優點,她站在我身旁練朗誦、跳舞和唱歌。
 有人告訴過我我們像姊妹,也有人告訴過我們像雙胞胎,更有人告訴過我我們像油炸鬼。我不太信星座,因為我跟本解釋不到,為何巨蟹座的她,會和我這樣要好。
有人告訴過我我們像姊妹,也有人告訴過我們像雙胞胎,更有人告訴過我我們像油炸鬼。我不太信星座,因為我跟本解釋不到,為何巨蟹座的她,會和我這樣要好。

~待續~